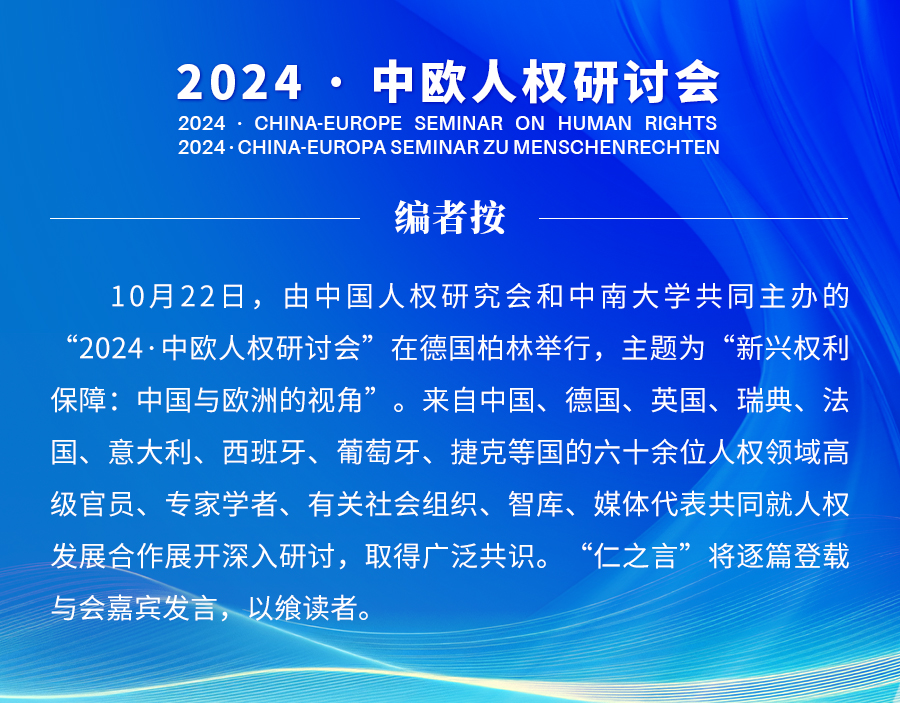
气候人权的反思与重构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唐颖侠
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关系无疑是最为热门的一个话题。气候变化诉讼正在迅速增长,据统计数字,现已有超过2600例案件。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的诉讼案例,从数量上来说并不是最多的,但是从发展的势态上来说却是最快的。气候变化诉讼的迅猛发展是国际对气候变化谈判机制的缺乏以及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不足的一种回应。但是,我认为应对气候人权做一个冷思考。
当我们讨论气候人权的时候,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从何种意义上去界定气候人权。气候人权同时兼具政治维度和法律意义的双重属性,区别政治和法律这两个不同的维度,有利于厘清概念,避免错误的解读和盲目的乐观。既不要用政治意义上的气候人权的方法论证,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具有明确法律义务的概念;同时,也不要用法律意义上的气候人权的概念和方法掩盖气候人权在政治维度上发挥着的重要推进作用。气候人权的政治化建构化解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分歧,逐步在应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以及意愿,从而催生了健康环境权的全球兴起和在联合国层面的承认。因此,应当在不同的语境之下解释气候人权的概念。
首先,在政治维度上的气候人权概念。政治话语具有建构的功能,通过概念的塑造和强化,引发公众的关注,从而形成变革性的政治力量。其中有三个推动力量和途径:
从国家主导角度来看。2005年因纽特人在美洲人权委员会提起申诉,这是首次用人权方法来解决气候变化的尝试,尽管这个案件被驳回而告终,但是它成功地赋予了气候变化一个人类的面孔。这表明气候变化不仅是自然领域的变化,也是一个人为的过程,这是气候变化第一次作为人权的出现。马尔代夫政府就抓住此契机,在因纽特人造势的基础上,时隔两年,2007年在马累召开小岛屿国家的会议,签署了《马累宣言》。而《马累宣言》是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了气候变化和人权之间的相关性的国际性文书。后将其作为一项紧迫的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0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回应,即第7—23号决议《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决议》,首次在联合国文件中承认了气候变化和人权的相关性。
从专家推动型模式来看。第一,以联合国特别机制为例,继2008年第一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做出之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与人权的决议,更关注到气候变化对特殊群体影响。第二个推动力量来自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09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首次推出了第一份关于人权与气候变化的报告,详细阐述了气候变化可能对于人权构成的各种各样的威胁。第三,除了人权的机制之外,联合国其它机制也在共同推动这一力量。
从受害者驱动模式来看。这种模式主要通过战略性气候变化诉讼来实现,所谓战略性气候变化诉讼,它不是只针对个案而言,而是要超越个案的影响,而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影响诉讼。这里面主要是四种方法:第一,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第二,执行现有的承诺和目标,各个国家应当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执行立法。第三,各国采取气候变化行动的时候,也要保护人权,国家的消极义务要求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本身不能助长对于人权的侵犯。第四,针对公司的诉讼,绝大多数基于人权的气候变化诉讼都是以政府作为目标被告。主要基于人权在传统意义上它的义务承担者是以国家为中心的。
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气候人权,存在着三个难以克服的法律障碍。第一个障碍,因果关系。气候变化是一种气象的现象,本身它并不侵犯人权,气候变化不是由一个单一的污染者所引发的,也不限于今天对于全球变暖所做出的影响。第二个障碍,诉讼主体资格的障碍或者受害者的障碍。寻求以侵权行为补救的原告必须要证明作为或者不作为这样的侵权行为侵犯了所依赖的依据,无论是人权公约,还是国家法律当中作为一个受害者的地位。第三个障碍,域外管辖权障碍。人权公约的地域适用范围无论是ICCPI还是ICCSR里面都有明确规定,必须在领土的范围以及其管辖的范围之内使用,而气候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具有全球性。
在气候人权的过度扩张中可能会带来风险。人权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追求所有政治或者道德目标的理想工具。人权的过度扩张可能会最终削弱它的合法性和接受的程度,反而损害到人权的整个目标实现。人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的概念,而它的生命力和持久性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如何回应现实社会当中的需求,并且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接受。因此,避免对于单一人权规范做广泛的无边界的解释,从而导致权利的冲突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导致碎片化和空心化。我们有必要重构气候人权的概念,并且明晰它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的维度。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3980号